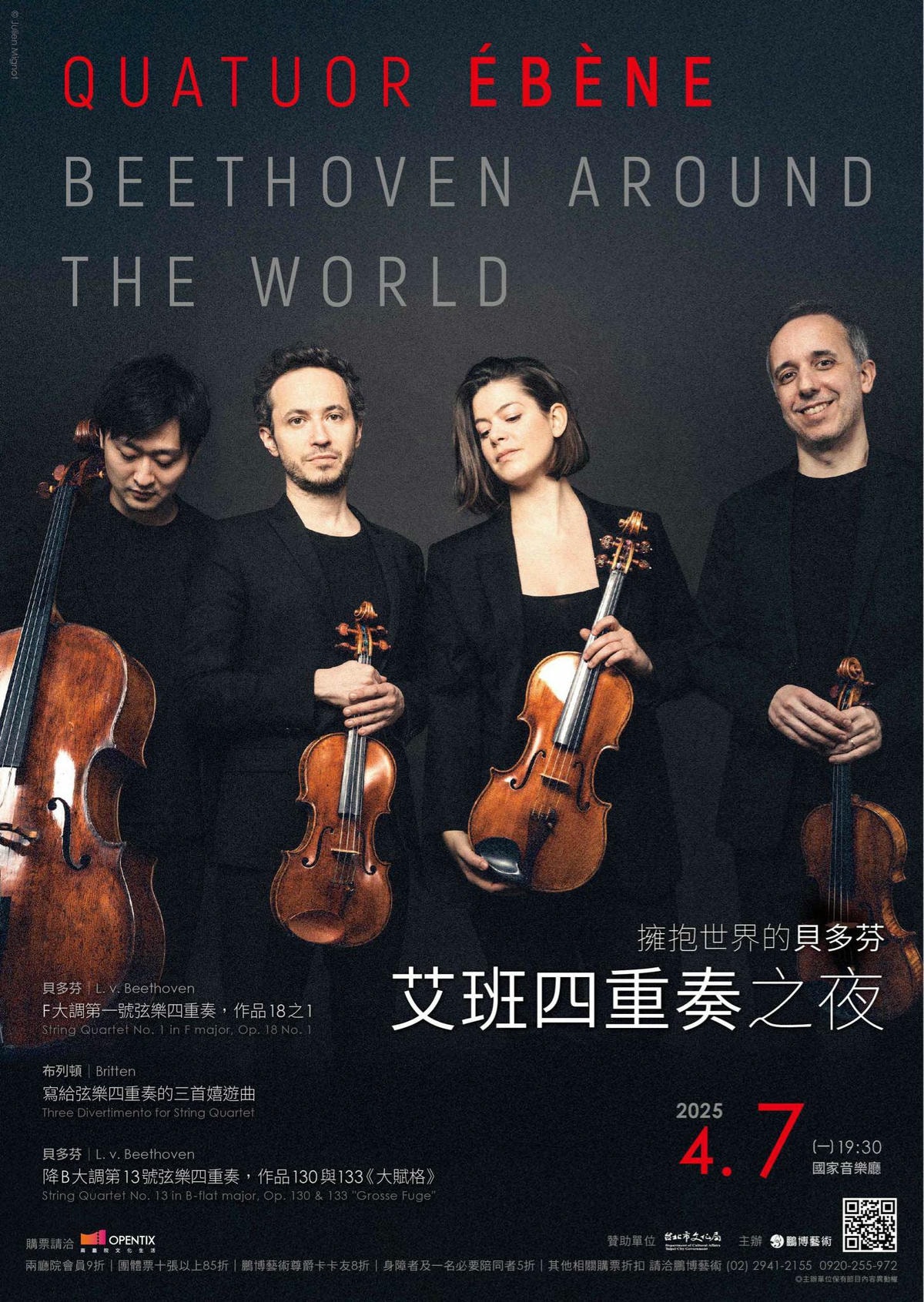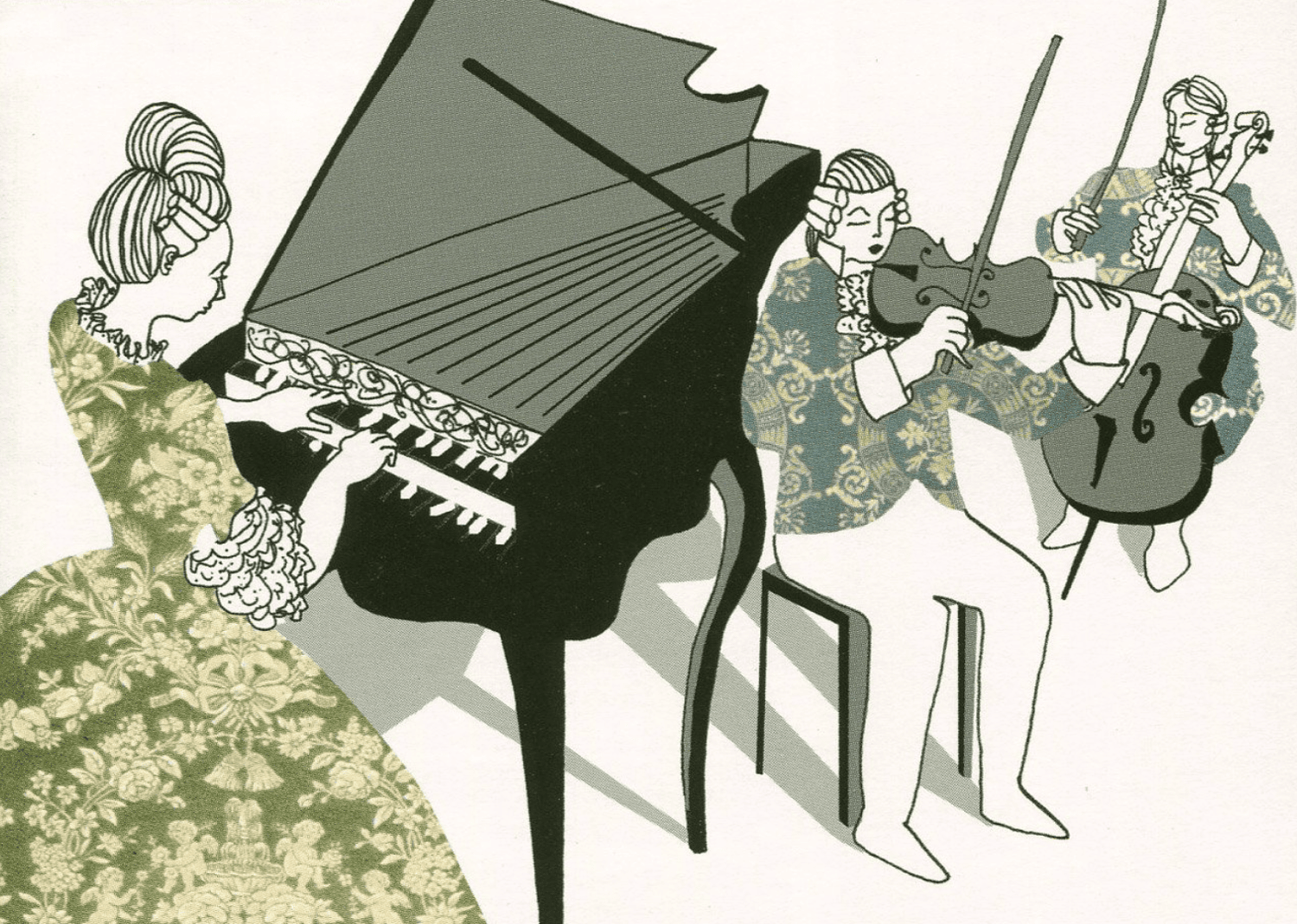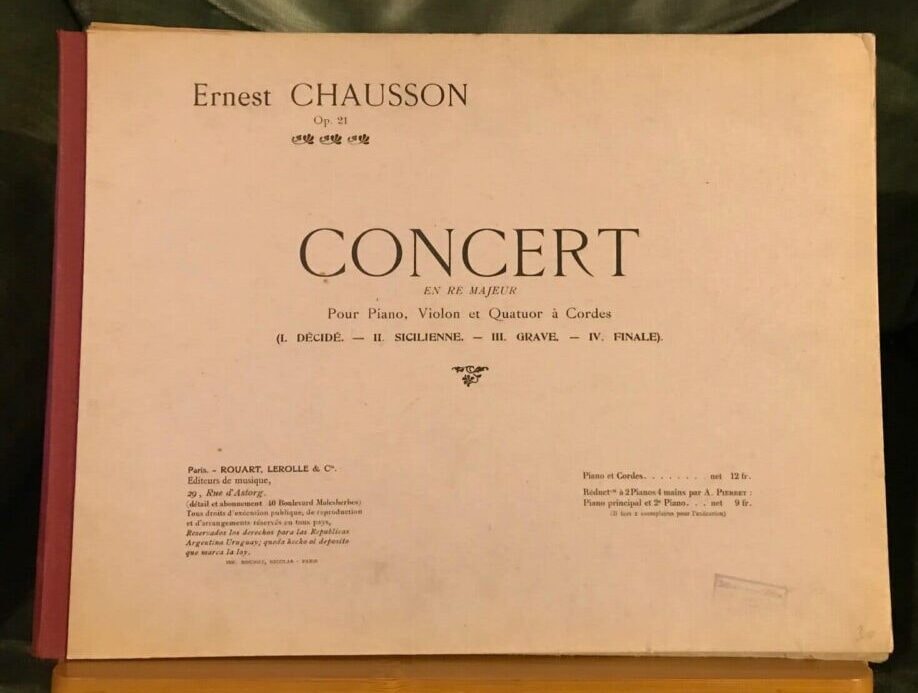拉威爾:《G大調鋼琴協奏曲》
(2025年10月15日「捷克愛樂管弦樂團在台北演出的樂曲解說)
一次大戰後:狂熱年代的新古典主義傾向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,拉威爾曾往前線,被編入軍車部門;戰後他持續的活躍於音樂界,直到1937年辭世。德布西則在1918年「一戰」結束的前幾個月病逝了。拉威爾晚年所經歷將近二十年的「二戰期間」,是個全新的時代;這個戰後人們劫後,社會期盼得到復甦的時期,大家放縱、歡騰著,而被俗稱為「狂熱年代」(Années Folles)。狂熱年代的法國音樂,正如當時在「帶風向」的一位藝術家柯克多(Jean Cocteau)所言:「我希望音樂家們為我“建造”一種音樂,適合我“居住”在其中,就像我住在房子裡一般」。
也就是說,音樂就像當時其他的藝術般,講求實際、舒坦、直接,不要再像一戰前「美好年代」那麼繁富、多變化,那麼多層次,那麼放任、不著邊際——柯克多還說:「別再創造些讓人雙手抱著頭聽的音樂」,意謂著深奧、難懂的音樂。狂熱年代的藝術體現出生靈活現的「新精神」(Esprit Nouveau)——「新精神」一詞,被當時最有創意的建築師勒·柯比意(Le Corbusier)當做他創立的藝術雜誌名稱之後,成了那個時代文藝界的口號。

就像比他年長的薩悌(1866-1925),比他稍年輕的斯特拉溫斯基(1882-1971),或比他年輕許多的「法國六人組」一般,拉威爾與他的同僚們一起,在狂熱年代迎向了「新精神」,而告別了一戰之前「世紀末」音樂的繁複、脫離現實。現實世界中,歌廳、秀場、馬戲團的通俗音樂、舞曲,被應用到創作中,歡騰、喧鬧、活潑的聲響背景,成了新時代的韻律,被體現在音樂中;運動、休閒、娛樂的種種「動態」(movements),被轉化成音樂;火車、飛機等交通工具,工廠裡頭機器運轉的奇特音響,成了「機械音樂」(musique machiniste),或音樂創作的「機動效應」(motorisme)。
然而所有這些新時代、現實世界的效果,經常被表達的相當單純、清晰、簡明、直接;為了達到這些效果,作曲家們避開了整個十九世紀的浪漫與後浪漫,回溯到十八世紀古典時期之前比較單純、客觀的語法,使得「新古典主義」的傾向,成為狂熱年代音樂創作的主要潮流。新古典主義嘗試在復古中創新,一方面回到古典時期以前的較小的編制、格局,講求勻稱、平衡的形式、句法,避免浪漫、後浪漫到「世紀末」音樂的激情、繁複;另方面則是讓上述的種種「新時代」現實世界的音響,滲入、融進新古典的框架之中。
具有古典形式與精神的《G大調鋼琴協奏曲》
拉威爾同時在1929年底開始創作的《G大調鋼琴協奏曲》與《D大調鋼琴協奏曲「左手」》,雖是成對的協奏曲,曲風上卻大異其趣,「G大調」充分體現狂熱年代歡騰的「新精神」,「D大調,左手」卻回憶著一戰深沉的不安——那是為戰時失去右手的奧國鋼琴家維特根斯坦(Paul Wittgenstein)而創作的。這對「孿生」的協奏曲,與稍後完成的歌曲集《唐吉訶德致杜爾希娜》(1933年),同是拉威爾最後的創作——在那之後,他受腦疾所苦,到1937年辭世,不再創作。
《G大調鋼琴協奏曲》1932年在作曲者親自指揮「拉慕柔管弦樂團」(Orchestre Lamoureux),在巴黎首演;由女鋼琴家瑪格莉特·隆(Marguerite Long)主奏。稍後兩人一起展開歐洲巡演,獲得盛大的成功。
此曲由於充分乞靈於莫札特,以及古典傳統的形式、表達方式,而顯得相當「新古典」。拉威爾親自解釋道,他想創作一首具有莫札特或聖桑斯精神的協奏曲:「我想使它具有歡愉、亮麗的效果,而不須朝著深沉與戲劇性去發揮。最初我甚至打算稱此曲為《嬉遊曲》( divertissement )⋯⋯」。
此曲快、慢、快的三個樂章組構,木管「二管編制」不太大的樂團,鋼琴與管樂器充分、靈活的互動有如嬉遊曲般的效果,刻意的迴避或減緩「發展手法」的戲劇性起伏,相當規則的分段、分句,這些特色都體現出古典精神。拉威爾更進一步的解釋,無疑提示著此曲中到處浮現著的「新精神」:「此曲與我的《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》息息相關,它們都受到爵士樂的啟發,但使用的相當節制」。
1926年美國音樂家蓋希文前往巴黎,曾拜訪了拉威爾;拉威爾無疑見識了蓋希文稍前完成的《藍色狂想曲》(1924)與《F大調鋼琴協奏曲》(1925) 。1928年拉威爾曾前往美、加巡演,更有機會直接見識到美國的爵士樂、藍調音樂(blues)。
第一樂章:2/2拍子,G大調。奏鳴曲式「欣快的」(Allegramente)
第一主題區,宛如體現出「狂熱年代」的歡騰;與第一主題區形成對比的「變慢變沉」(Meno Vivo)
第二主題區,藍調音樂略帶憂鬱的抒情歌唱,彷彿是「新時代」的鄉愁。
「拍板」(whip)猛擊一聲,短笛導出了簡短、喧鬧的第一主題區;在其間,管樂器的活潑交錯成鮮艶的色彩,高、中音弦樂的撥奏,低音弦樂器的震音(tremolo),定音鼓的滾奏,共同經營出來的生動效果,在鋼琴的烘托下,浮現著現代社會的律動。鋼琴雙手彈出的琶音,右手在白鍵上滑動著(G大調),左手貼在黑鍵上遊移(升F大調),如此而形成兩個不同的調彼此摩擦著的「複調」(polytonality)鮮明效果。鋼琴快速朝上、朝下的「滑奏」(glissando),是爵士樂中慣用的奏法。
英國管獨奏導引出鋼琴獨奏,呈現出無精打采、徐緩歌唱著的第二主題。鋼琴在木管與加弱音器銅管的伴奏下,以及爵士樂不規則節奏的推動下,將藍調旋律的憂鬱,渲染得越來越高昂。速度變快,音樂進入發展部,先是第二主題,然後是第一主題的動機,被作為擴充、延伸的材料。
鋼琴從發展部開始的明顯炫技,無疑受到聖桑斯鋼琴協奏曲的啟發——華麗的效果受到古典精神的節制,展現出十足的法式優雅;也使得美國爵士樂的野性,被加以適度地馴服。速度變慢,第二主題清晰的再度浮現,那是再現部的開始。在豎琴為主的伴奏下,第二主題被重寫的充滿著細緻微妙的變化。
再現部尾端,藍調的旋律逐漸轉化成一小段只由鋼琴獨奏、鑲嵌著細微裝飾音的「裝飾奏」(Cadenza)。第二主題再被樂團總奏充份擴大到頂點時,速度變快、變活潑,第一主題被鋼琴以跳奏呈現出來,與樂團合奏出強勁的尾聲。
第二樂章:充分的慢板,3/4拍子,E大調
拉威爾曾向瑪格莉特·隆表示:「(創作此樂章時),我兩小節、兩小節的一直寫下去,藉助於莫札特單簧管五重奏(的慢速樂章)。」
莫札特《單簧管與弦樂五重奏》(K. 581)第二樂章「小廣板」(Larghetto)中,由單簧管主奏的縹緲旋律,的確是以兩個小節為單元,平順、柔婉地串連起來的。拉威爾卻乞靈於如此古典式的飄忽的旋律,將它轉化成二十世紀初「阿拉貝斯克」(arabesque)式的旋律——有如爬蔓植物輕靈的莖葉,自由地朝高處延伸著;在微風吹拂下,失重般的飄浮著。
在沒有任何伴奏之下,鋼琴淺吟低唱的獨奏出三十三小節的阿拉貝斯克;右手以3/4拍子帶出自然音的、沒有張力的、飄逸的旋律,左手卻以3/8拍子彈出三個八分音符為一組、一再反覆的、浮動著的節奏型;兩種不同的三拍子疊在一起,共同交織著搖籃曲般的夢幻與遐思。
鋼琴獨奏的顫音,彷彿把樂團喚了進來:長笛、雙簧管、單簧管、低音管相繼加進來,各種管弦樂器的交錯出現,一方面做出細微的色彩變化,另方面藉著不協和的音響,好像把自然音的旋律給推擠了,或給嚇著了,而讓主旋律飄得更高、更遠,如此而形成了很自由也很含蓄的、廣義的「複調」的效果。
接著鋼琴藉著連串六連音的裝飾效果,將主旋律分化得更加輕靈、飄浮,管弦樂也被處理得更緊湊,而將音樂帶入心靈迷醉的高點。主旋律在此樂章的主調E大調上重現,在鋼琴八連音音型的烘托下,由英國管獨奏出來之後,這整個重現段逐漸擺脫了先前的不協和與繁複,最後平靜安詳地,在鋼琴漸弱的顫音中結束。
第三樂章:急板,2/4拍子,G大調
比第一樂章更加緊湊、有衝勁,而將狂熱年代的歡騰炒得更加熱鬧生動。爵士樂般的不規則、切分音節奏,長號的滑音,短小音型的機械性反覆,不協和音響與複調的含蓄應用,被用來體現上個世紀20、30年代都會生活的忙碌意象。四個強烈、突兀的和弦,不只敲開了這個末樂章,還一再出現,將呈示部的三個主題分隔開來。
第一主題是鋼琴獨奏在十六分音符上的使勁、狂奔,並且與單簧管、短笛、長號的競勝。第二主題是幾個短小的音型,各自快速的反覆著,宛如機械、交通工具不停運轉著,所產生的「機動效應」(motorisme)。第三個主題彷彿是一段刻不容緩的進行曲,將時代的巨輪往前推進著。
在發展部,低音管獨奏出一長串的十六分音符的「無窮動」(Perpetuum Mobile)段落;這個有如鏈帶快速、流暢運轉著的段落,被鋼琴接了過去,當做炫技來發揮。從發展部到再現部,先前出現過的一些音型的自由重現、改寫,渲染出機械時代繁忙生活,一切欣欣向榮的頌讚。結尾處,開頭的四擊強勁和弦的重現,好像為樂曲的結束劃上四個驚嘆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