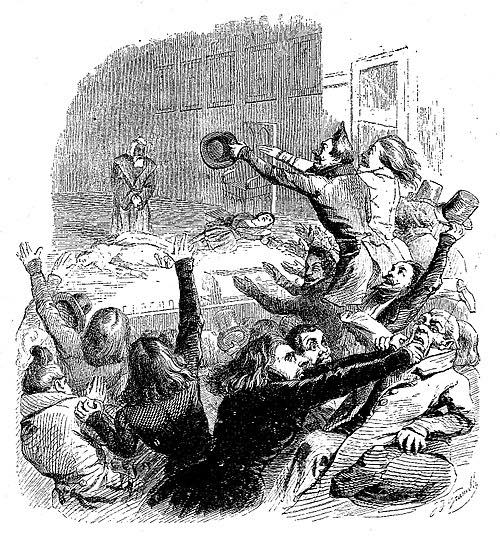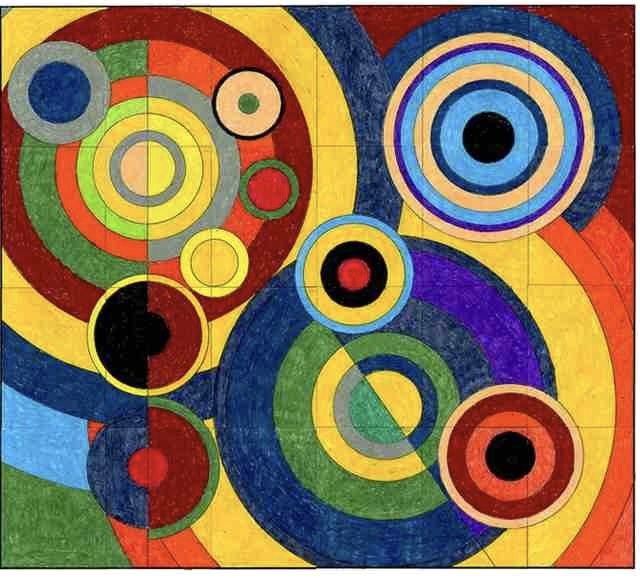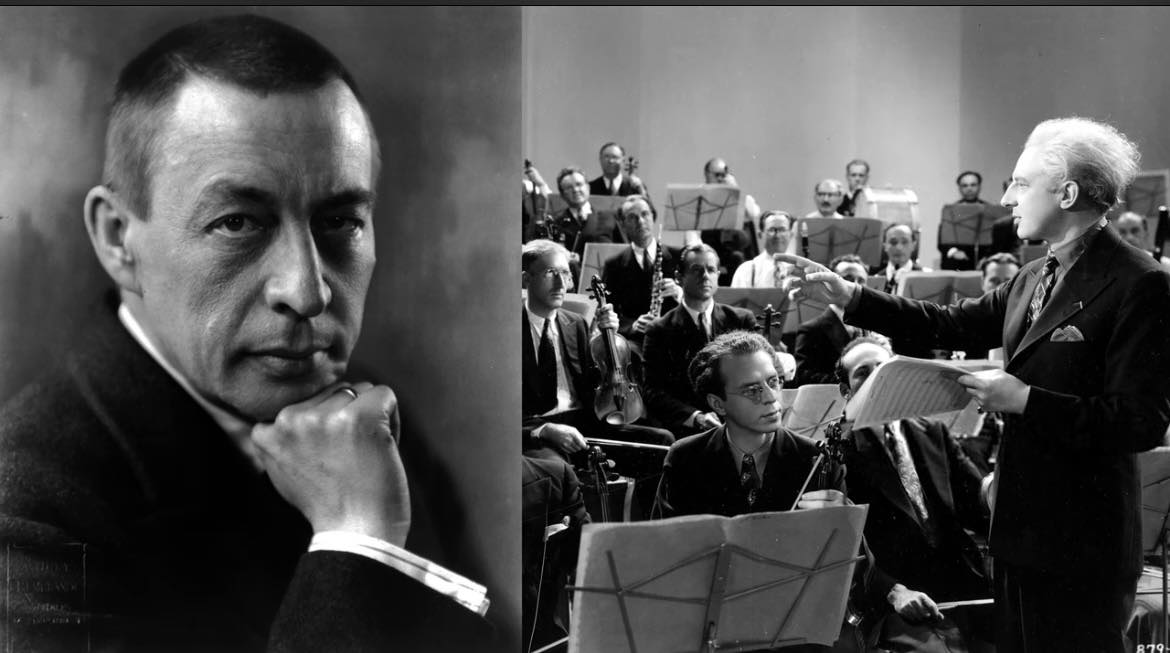白遼士《幻想交響曲》
前言
幾個星期前,巴黎管弦樂團在高雄、台北演出,有幸為這三場管弦樂音樂會撰寫樂曲解說。感謝主辦單位「巴哈靈感」讓我有機會盡情發揮,不拘字數的將每首樂曲介紹的比較完整。接下來幾天,我將按照樂曲創作年代,將這些「曲解」一首一首的貼岀來,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:白遼士《幻想交響曲》,聖桑斯《第三號交響曲「管風琴」》,柴可夫斯基《小提琴協奏曲》,穆索斯基/拉威爾《展覽會之畫》,拉威爾《庫普蘭的禮讚》(一般譯為「庫普蘭之墓」),拉赫瑪尼諾夫《第四號鋼琴協奏曲》,布列茲《起始》。
白遼士的《幻想交響曲》,由巴黎管弦樂團的前身「巴黎音樂學院管弦樂團」舉行首演,因此可說是「巴管」的招牌或驕傲。該曲首演時,第四樂章「赴刑進行曲」才剛奏完,現場聽眾們高聲喝采,要求馬上再奏一次。充滿著殺伐之氣的第四樂章,十足體現出1830年「七月革命」的肅殺氛圍,正如同一年繪成的德拉克瓦的畫作《自由女神引導人民》一般。
白遼士:幻想交響曲,作品 14

《幻想交響曲》首演的1830年,是法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。那一年,正好也是雨果的成名作,戲劇《艾納尼》(Hernani)激起輿論的年份;而在相同的時候,德拉克瓦的名畫《自由女神引導民眾》使他聲名大噪。我們知道該畫是根據同一年爆發的「七月革命」繪成的。1830年是浪漫風格藝術在法國興起的標竿年代,同時也是整個歐洲的藝術,從浪漫初期過渡的浪漫中期的年份 – 十九世紀初,在日爾曼與英國已發展成形的浪漫藝術,開始影響到法國,此後的十幾、二十年之間,巴黎成為浪漫藝術發展的中心;在音樂界,1830年前後,白遼士、李斯特、蕭邦先後來到拿破崙戰爭平息下去之後的「歐洲首都」,展開他們的藝術生涯。
《幻想交響曲》首演時的年輕白遼士(1803-1869),還是巴黎音樂學院的學生;他那近乎病態的敏銳、善感、狂飇,使得認識他的一位晚輩古諾,在日後回憶道:「對白遼士而言,所有的印象,所有的感覺都必須走向極端;無論歡樂或哀傷都成了他的譫妄。」 白遼士前往觀賞一個英國劇團,演出莎士比亞戲劇時,愛上了該團的主要女演員史蜜遜(Harriett Smithson),這是大家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。
然而,究竟他愛上的是史蜜遜小姐,還是她所扮演的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女主角歐菲莉亞呢?既然白遼士都不曾在舞台以外的地方見到史蜜遜,後來很快就鬧失戀了,所以他比較是愛上了莎翁名劇中的永恆女性吧!不論如何,這段不可思議的迷幻,戀情,卻成就了千古絕唱《幻想交響曲》,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更浪漫呢?
《幻想交響曲》首演的前十天,白遼士設法在某報刊上登出此曲的「文字說明」(programme),用來解釋樂曲想要表達的內容,而激起群眾們的好奇,促成了首演的成功。這個在當時非凡的舉動,其實是日後「標題音樂」(musique à programme)這個稱法的濫觴。必須附帶說明的是, musique à programme 一詞被譯為「標題音樂」,很容易引起誤解,以為它指的只是音樂的標題,事實上不是如此,除了標題之外,它還包括了每個樂章相關的文字說明(見此文下方每個樂章的解說)。 programme 一詞指的不是標題(title),而是文字說明,例如一直到今天,音樂會的節目册在西方,一直被稱為 programme,因為册中主要是有關該音樂會相關的介紹,以及樂曲解說。
《幻想交響曲》1830年12月5日在巴黎音樂學院的音樂廳,由哈伯內克(François Habeneck)指揮該校的管弦樂團首演。在那之前,白遼士已陸續聽過該團演奏的貝多芬第3、5、6、7 這四首交響曲,那是貝多芬交響曲在巴黎的最早演出;白遼士深受貝多芬直接啓發影響之際,還開創出他那獨樹一幟、標題音樂式的交響曲。貝多芬交響曲中,相同的動機在不同樂章中再現的處理方式,促成了白遼士「循環復現概念」(concept cyclique),使得不同樂章彼此呼應,在充分變化中營造統一感。白遼士將他的交響曲中,不同樂章復現的主題或動機稱為「固定樂思」(idée fixe),該詞法文的、心理學式的原義是「頑念」的意思。
《幻想交響曲》中的固定樂思,其實就是「愛人的主題」 – 一位失戀藝術家想吞食大量鴉片自殺,不料份量不夠,讓他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。在幻覺裡,愛人的幻影不時的浮現,一再的糾纏、折磨著他。
在標題(文字說明)激發下,白遼士適度的擺脫了傳統四個樂章交響曲的框架,而以五個樂章,每個樂章都藉著別出心裁的音樂,呈現出自由、新穎、獨特的意象,如此而為日後文學與音樂的融合建立了典範。在文字說明觸發的想像之下,某些創新的音樂安排,在當時簡直是異想天開,例如第三樂章「田野的情景」,雙簧管的獨奏者先是在舞台後方演奏,以便和舞台上的英國管遠距離的對唱,用來營造充分的空間感。某些當時甚少被使用的樂器,諸如豎琴、短號(cornet)、鐘、歐菲克列伊德低音號(ophicléide))等,被用來渲染獨特的音響與色彩。
白遼士因此成為管弦樂的調色大師,致力於研究、開發各種樂器組合的可能,藉樂器的色彩、音響變化,來增益他的音樂表現性;不只他的管弦樂創作,還有他的文字著作《管弦樂法》,兩者相得益彰的對後世造成深遠的影響。以下是《幻想交響曲》每個樂章「文字說明」的概要,以及各樂章的音樂特徵。
第一樂章:夢幻 – 激情。
「一位年輕藝術家,在熱情沖擊下,迷戀上一位集媚力與完美於一身的女人… 在鴉片的作用之下,狂熱、嫉妒、柔情、眼淚、宗教的慰藉,全混合在一起,匯流成緊抓住他的激情譫妄。」
一開始廣板(Largo),4/4拍子,C小調的導奏,表達的是理想、完美愛情的憧憬,它那柔美、多愁善感的旋律,源自早熟的白遼士十二歲時譜寫的一首《艾絲特拉的浪漫曲》(Romance d’Estelle) – 該曲是少年的白遼士,用來懷念一段沒有結果的初戀。加弱音器的小提琴以小調緩緩唱出主旋律,逐漸帶往熱切的高點,又慢慢緩和下來,體現出「憂鬱的夢幻」之後,音樂才過渡到C大調、2/2拍子、激動且熱情快板」的奏鳴曲式主段,用來炒熱「激情」。
第一主題其實是剛剛浪漫曲旋律的復現與變化,這個「愛人的主題」,將成為全曲五個樂章一再重現的「固定樂思」。處理的相當自由的奏鳴曲式主部,簡而言之,呈示部的第一主題區如果是由固定樂思(A段)擴充而成的,第二主題區則是體現激情的B段。發展部又從A的變形開始,由體現嫉妬的C段延續成另一個高潮。再現部一樣從A段的變形開始,擴大成D段各種情緒交混、哀傷失望的激烈頂點,音樂才逐漸緩和下來,轉變成嚮往著宗教的慰藉。尾聲最後結束於固定樂思詳和的復現,以及宗教屬性的「變格終止」(plagal cadence)。
第二樂章:舞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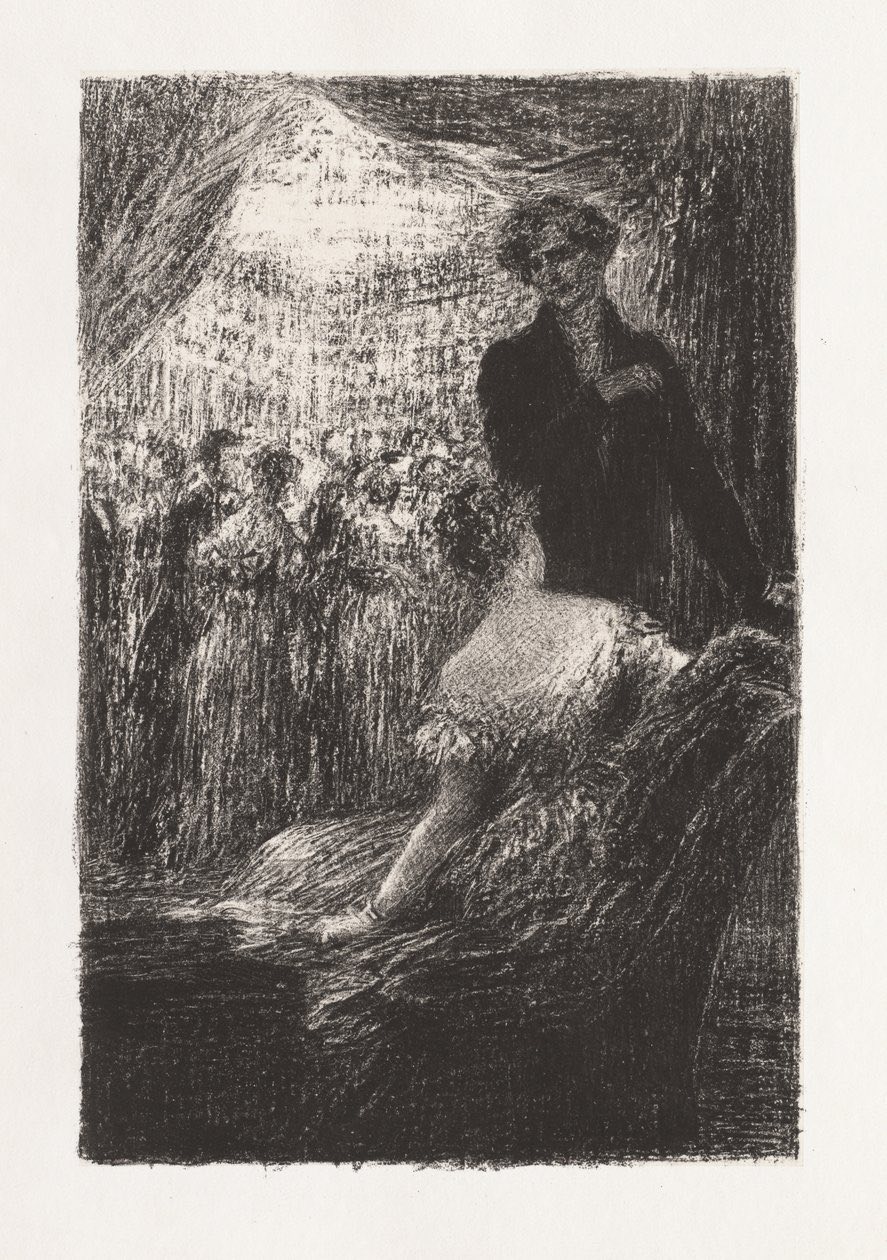
(《幻想交響曲》第二樂章)
「藝術家幻想到他處身於各種場合。例如來到一場舞會之中,沈迷在喧騰的歡樂裡…. 不料愛人的影像卻浮現出來,擾亂了他的內心。」
A大調,3/8拍子。一般交響曲的詼諧曲樂章,在此被圓舞曲取代了。衣香鬢影,水晶吊燈柔合光影下的廣濶、優雅的社交空間,被豎琴細緻的琶音,以及颯颯作響的弦樂震音(tremolo)渲染出來。樂舞酣暢,在舞曲的漩流中,固定樂思的兩度浮現,令藝術家越來越張惶失措。
第三樂章:田野的情景。
「夏日傍晚時分的鄉下,兩位牧人對唱著牧歌。藝術家踽踽獨行其間,愛人頑念的出現攪亂了平靜」。「後來,牧人之一再次唱起牧歌,卻得不到另一位牧人的回應… 遠方傳來的雷聲… 孤獨… 沈寂…」 。
慢板,F大調,6/8拍子。牧人對唱著牧歌的情景,顯然受到貝多芬《田園交響曲》末樂章「牧人們的感恩之情」的啓發。在這裡,以雙簧管與英國管的對奏,體現對唱的情景。雙簧管在舞台後,英國管在舞台上,此起彼落的呼應,帶開來的田野空間感,被藝術家徜徉其間的「幸福的主題」擴大了;該主題一再重複出現、變化,音樂一直被擴充的更寬濶,直到固定樂思的出現、擾亂,才消沈下去。音樂最後結束於得不到回應的英國管獨奏,以及定音鼓小聲滾奏的雷聲之中。
第四樂章:赴刑進行曲。
「藝術家幻想著殺死了愛人,被判極刑,被帶往刑場。愛人頑念的柔美旋律被單簧管奏出,卻被樂團奏出的强烈和弦打斷了,那是儈子手的斧起刀落,人頭落地。」
不倉促的小快板,G小調,2/2拍子。這是全曲五個樂章中,「多岀來」的一個樂章,一般四樂章交響曲所沒有的。帶著殺伐之氣的進行曲、行刑的場面,回顧著從大革命一至到拿破崙戰爭之後嚴峻的時代背景。整個樂章主要由兩個進行曲的主題一再交錯、擴充而成。第一個主題是G小調的,一個往上大跳之後,連續下降的強勁、陰沈的旋律,主要由低音樂器奏出,意味著邁向死亡。另一主題是降B大調的,主要由銅管樂器奏上昇、高昂的旋律,那是赴刑進行曲的本身。肅殺之氣被炒熱到極點,固定樂思才剛出現之際,人頭已滾落,鼓號冷酷無情的高鳴著。
第五樂章:群魔夜會之夢。
「藝術家夢見身處地獄中。所有的幽靈、怪物、亡魂、巫師與魔鬼,都前來繞著他狂舞。愛人現身後變形、狂笑、蹦跳、爛俗、詭異,簡直是娼妓!… 鐘聲響起,群魔的亂舞稍歇,他們俯身傾聽末日經(Dies irae)的樂聲。稍後夜會的輪舞又重啓,與末日經的音樂攪混在一起,捲起可怕的渦漩。」
弦樂細分成十二個聲部,奏出輕微、神秘、詭異的音響,緩緩開啓了不協和、陰沈的導奏。二十餘小節後,音樂進入E小調、充分的快板,6/8拍子的段落。固定樂思成了怪異的化身,被套入輪舞的節奏中。午夜的喪鐘響起,相繼響了十二次,首演時使用的是教堂中使用的銅鐘,近代的演出才用編鐘取代。中世紀聖歌「末日經」的旋律,在白遼士的時代是用軍樂隊中使用的歐菲克列伊德低音號(ophicléide)獨奏,後來才用新發明的低音號(tuba)取代。
末日經威嚇的主題被套在輪舞狂烈的韻律上,經過數次重現、變化,最後主題被當做材料,譜成一大段壯濶、自由、鬼哭神號般的賦格,用來體現那位自暴自棄的藝術家,不由自主的被捲進群魔亂舞的漩流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