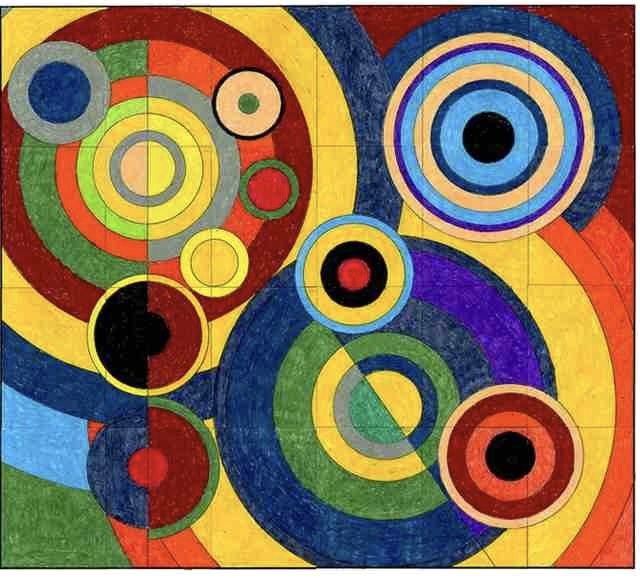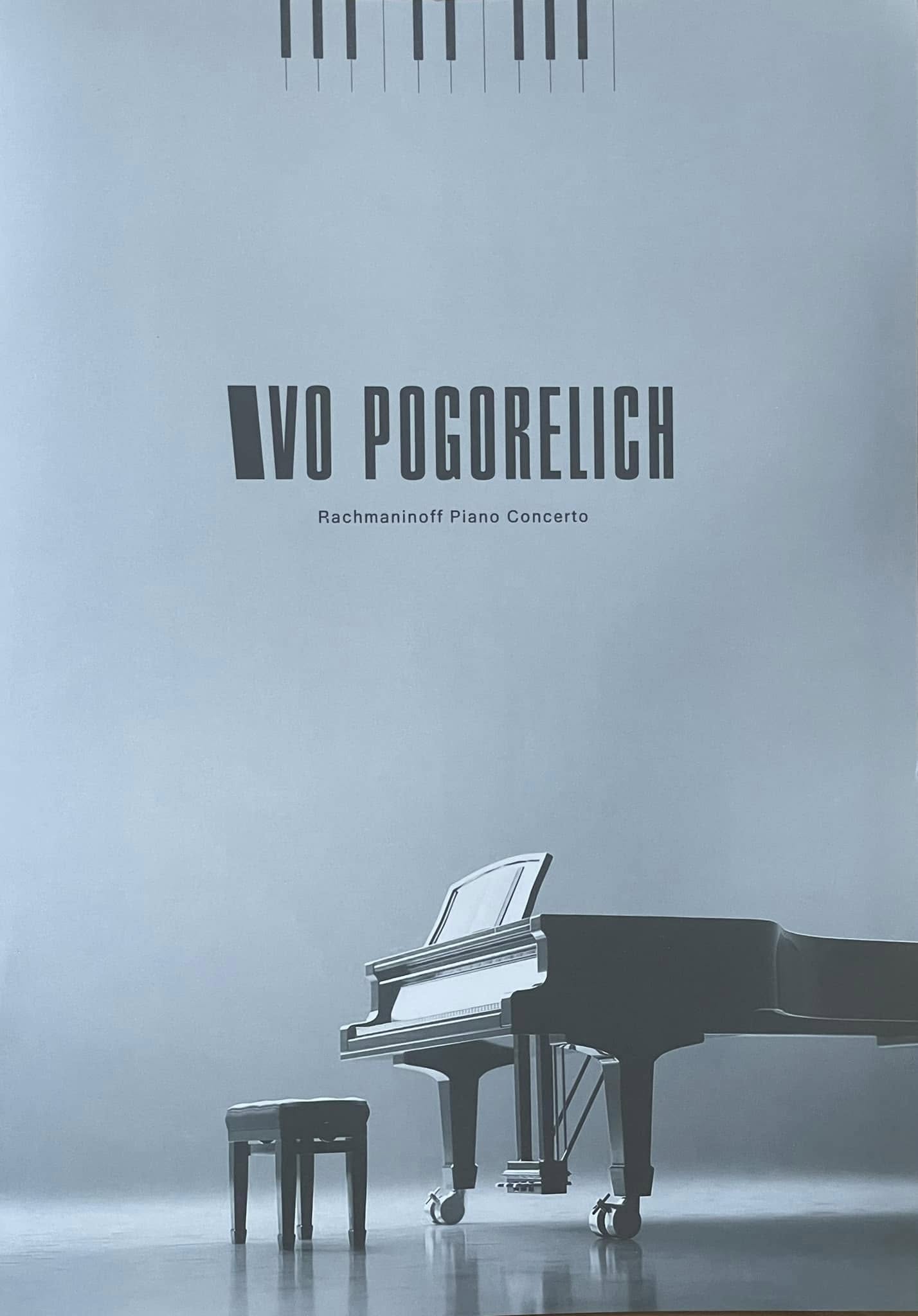布瑞頓(1913-1976)《戰爭安魂曲》
前言
前天(2020.02.28)「二二八」,高雄衛武營演出了英國作曲家布瑞頓(Benjamin Britten)的《戰爭安魂曲》(War Requiem, 1962年)。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,將我寫的一篇簡短的樂曲解說貼出來,供大家參考與指教。
布瑞頓:戰爭安魂曲
二十世紀前半的兩次世界大戰,成了人類空前的浩刼。戰後人道主義的不彰,大、小爭端仍舊不斷;在此世界的前途仍舊籠罩著陰霾之下,英國作曲家布瑞頓(1913-1976)創作的《戰爭安魂曲》,成了史上以戰爭為題材的至高傑作;它於1962年首演於柯文垂主教堂(Coventry Cathedral)重建完成的場合 – 這座中世紀的著名古蹟,二戰即將結束之前,遭空襲摧毀。

《戰爭安魂曲》以天主教的安魂曲為經,以一戰期間陣亡的詩人歐文(Wilfred Owen, 1894-1918)的詩作為緯,織造成一部兼融宗教性與通俗性,有如史詩般恢弘壯濶的鉅構。全曲七段音樂,每段各自以一經文與歐文的詩句相呼應,巧妙的渲染出兩方面相得益彰的效果,例如第二段〈末日經〉(Dies irae), 預示世界末日到臨時,天使號角齊鳴,喚起世人接受最後審判的驚天動地的宗教景象,與歐文的反戰詩作交織在一起:「軍號高鳴,使傍晚變得悲傷…..」。《戰爭安魂曲》因而不是一般戰爭音樂般的用來宣揚愛國主義,而是一再警告著全人類:只有避開不和與衝突,才能免除人世的悲慘與敗亡。
在應用「後浪漫」式的大編制之際,布瑞頓在此曲中一再讓三種不同層次的效果交替出現。第一種是室內樂般的效果,聚焦在歐文的詩作上,藉著兩位敵對陣營士兵的言詞(男高音與男中音),表達出戰爭的可怕與荒謬。第二個層次建立在安魂曲的歌詞上,以女高音、大合唱、整個樂團,體現出宗教式的、期盼世人靈魂的得到解脫與拯救。第三個層面主要由兒童合唱團與管風琴擔綱,它與人間的悲慘拉開距離,輕飄在天上,象徴著崇高的、靈性的境界。
將大編制的人聲與器樂,經營成上述三個分明的層次,布瑞頓無疑傳承著巴赫《馬太受難劇》的處理方式,當然也受到離他較近的馬勒的啓發。藉著如此的大編制,有效率的去製造對比、張力、戲劇性,布瑞頓不只受益於威爾第的《安魂曲》,還發揚了馬勒、霍爾斯特(Gustav Holst)的管弦樂法。廣泛的運用四度重疊的和聲,並且到處強調「三全音」尖鋭的音程,為此曲增添了許多新意。〈聖哉經〉(Sactus)段落中,閃爍著細微的音彩光芒,那是受到印尼峇里島(Bali)「甘姆朗音樂」(gamelan)的啓發。

第一段〈上主!求你賜給他們永遠的安息〉(Requiem aeternam)
喪鐘伴奏下,送葬行列緩緩前行(合唱),男高音唱出歐文的詩作〈被處死靑春的悲歌〉。
第二段〈末日經〉
如上文中敍述的,世界末日的號角聲,與歐文詩作的相互呼應:「軍號高鳴,使黃昏變得悲傷…..」(男中音)。
第三段〈那是痛苦流淚之日〉(Lacrimosa)
女高音唱出的經文,在喪鐘伴隨下,與男高音唱出詩句相糾結:「是什麼東西,助長了可鄙的陽光,使世界不得安睡?」。
第四段〈奉獻曲〉(Offertorium)
在管風琴琶音的伴奏下,兒童合唱團唱出對天界靈光的憧憬,男高音與男中音重唱著與之共鳴的歐文詩作。
第五段〈歡呼歌〉(Sanctus)
女高音與合唱團先後頌贊著神的榮耀 – 以荅里島甘姆朗音樂般的澄澈音響,最後由歐文的詩句做結束:「在來自東方的震撼之後…, 人的肉體是否能得到新生?」(男中音)。
第六段〈羔羊經〉(Agnus Dei)
合唱與管弦樂唱出的經文,與男高音為主的室內樂交錯出現,男高音唱出:「大家各自走著巔跛之路,最後都將通往各各他」。
第七段〈上主,求你從永死中拯救我〉(Libera me)
兩位敵對陣營的士兵,只能在死亡之後,在塵世之外得到和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