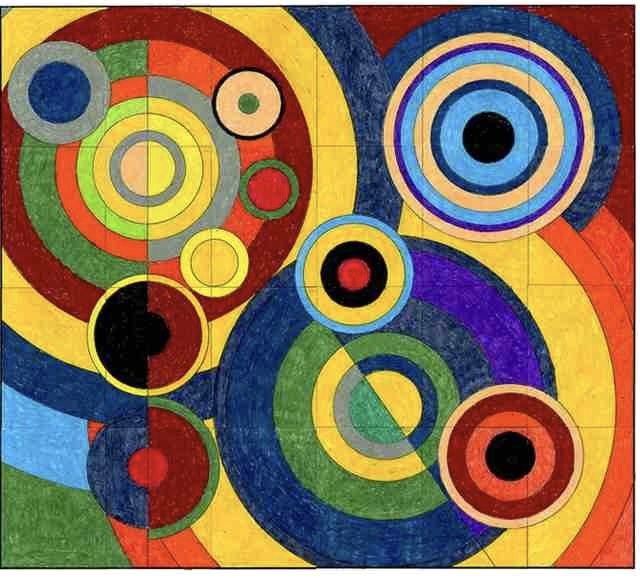貝多芬、葛令卡序曲、德弗札克交響曲、拉赫曼尼諾夫鋼琴協奏曲的樂曲解說
前言
前幾天的1月18日,鋼琴家波哥雷里奇與長榮交響樂團的合作,全場的曲目為:貝多芬的《費岱里奧序曲》,拉赫曼尼諾夫的《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,以及德弗札克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。一個多月前的12月8日,鋼琴家藍惠屏與高雄的「極地之光管弦樂團」同樣演出「拉赫二」與「新世界」,另加葛令卡的《盧斯蘭與魯蜜拉序曲》。有幸能為這兩場演出撰寫樂曲解說。由於曲目重複,我就「一魚兩吃」,省事多了。現在將總共四首樂曲的「樂曲解說」匯整在下方,一方面給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,另方面也給我自己留下記錄,供日後查閱。
 .
.
貝多芬:歌劇《費岱里奧》序曲(作品 72)
莫札特逝世於1791年,貝多芬則在1792年離開他的故鄉波昂,到維也納開創非凡的音樂事業;一則破天荒的事件,卻將這兩位大師各自所屬的創作時空劃分開來 – 法國大革命。在革命之前的「舊時代」中,音樂是為宗教與統治階層服務的;在革命後,音樂也將逐漸「民主化」了。
拿破崙繼承著革命的餘緒,想把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精神,靠著他的軍事行動傳播開來。在大時代的風起雲湧之中,自由思想擁護者的貝多芬,則藉著他崇高恢弘,且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音樂,去撫慰、激勵芸芸眾生受苦受難的心靈。拿破崙在野心的驅使下稱帝,而攻敗垂成,貝多芬則在困苦中奮起,成了法國作家羅曼·羅蘭所謂的「樂壇巨人」。
幾部貝多芬的傑作,與革命的母邦法國有著相當的關聯:「英雄交響曲」最初是為了稱頌拿破崙;「克羅釆奏鳴曲」原本是為當時法國知名小提琴家克羅釆而作;歌劇《費岱里奧》的情節,源自大革命的一件軼事。
貝多芬的唯一歌劇《費岱里奧》(Fidelio),它的劇本源自法國作家布伊(J. N. Bouilly)的劇作《蕾歐諾或夫妻之愛》(Léonore ou l’amour conjugal)。該劇敘述大革命「恐怖時期」的一段故事;貝多芬的劇作者為了通過當時尚屬君主政體的奧國當局的審查,而將這段「爭自由」的敏感故事背景,轉移到十七世紀的西班牙:弗羅列斯坦受陷害而被關進監獄,其妻蕾歐諾化裝成男人,改名為費岱里奧,設法混進監獄去拯救丈夫。貝多芬的歌劇最初被命名為《蕾歐諾》(Leonore),它於1805年首演未能獲得成功;此後貝多芬一再改寫,而在1814年定稿,改稱為《費岱里奧》。
在此漫長的改寫、一再被演出的過程中,貝多芬先後為它譜寫了四首不同的序曲 – 三首《蕾歐諾》序曲,以及一首《費岱里奧》序曲。目前演出此劇時,習慣的做法是,將《費岱里奧》序曲置於全劇開始之前,而將第三號《蕾歐諾》序曲置於全劇最後兩景之間,以預示劇情脫離了逆境與黑暗之後,逐漸迎向光明與希望的結局。
《費岱里奧》序曲,既非全劇劇情寫實的概述,也不把劇中重要的音樂段落綜合在一起,而是聚焦在女主角蕾歐諾之上,以器樂表達出女性帶頭爭自由的柔性與豪情。如此的意象,或許令人聯想到十多年後,法國浪漫畫家德拉克瓦(E. Delacroix)的名畫《自由女神引導人民》(1830年)。
整首序曲被自由的置入奏鳴曲式的框架中:短暫、快板的第一主題以E大調主和弦的分解和弦為基礎,藉著強勁的節奏,宣示出女英雄冒險救夫的決心。第一主題衍生而成,由法國號帶出的慢板第二主題,渲染著女性的柔情,以及女主角對愛情、理想的期盼。再度由法國號率先鋪陳開來的快速發展部,重申蕾歐諾堅定的意志,並預示著她即將遭遇的冒險患難。第一、第二主題短暫的重現之後,急板的激奮尾聲,彷彿預見了最後拯救行動的成功,以及爭取自由的勝利。
葛令卡:《盧斯蘭與魯蜜拉》序曲
在十九世紀前半,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,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音樂,當時有許多來自義大利、法國、德國的音樂家們,寄居在聖彼得堡、莫斯科謀生;俄國國內也還不存在培育專業音樂人才的正式學校,有志從事音樂工作的人,只能私下學習,或到外國留學。後來被尊稱為「俄國音樂之父」的葛令卡(M. I. Glinka, 1804-1857),正是留學生之一。
葛令卡1830年從義大利與德國遊學回俄之後,即應用俄國題材,適度的參考本土的民間音樂,先後創作了歌劇《效忠沙皇》(1836年)、《盧斯蘭與魯蜜拉》(1842年),成為俄國第一位重要的作曲家。葛令卡的歌劇具有些許俄國的色彩,本質上還是義大利式的;然而受到他的啓發,十九世紀中葉以後,俄國音樂的快速發展,將很快的趕上西方諸國,並且開拓出特性鮮明的前景。
葛令卡根據普希金的戲劇,譜成五幕歌劇《盧斯蘭與魯蜜拉》,1842年首演於聖彼得堡。全劇渲染著一段渲染魔法與幻境,英雄救美的傳說。劇中包容了韋伯式的劇情、法國式的舞蹈、義大利式的歌唱;某些描繪特殊情景的和聲效果,顯得相當有創意。此劇根據俄國作家劇作譜寫歌劇的做法,日後將引發仿效,例如柴科夫斯基的幾部歌劇。
《盧斯蘭與魯蜜拉》的序曲,簡潔而亮麗,散發著奔放的熱力,因而經常被當做管弦樂音樂會的開頭曲,一下子就能夠炒熱現場的氣氛。就像當時許多歌劇序曲一般,這首序曲將劇中的幾段重要的主題,置入於奏鳴曲式的框架中,以概括全劇的情節,預示全劇的氣氛:呈示部中,男主角盧斯蘭充滿活力而尚武的主題,成了第一主題;它與柔婉的第二主題,也就是「愛情的主題」,相互對照。
代表惡勢力的侏儒切諾摩的主題,則在中途介入攪局,掀起不安的情緒,成了發展部。再現部則是英雄救美的凱旋;侏儒的主題(長號)在尾聲中倉徨遁逃。葛令卡以下降的「全音音階」來描繪這個逃竄的情景,這可能是史上首次應用全音音階的實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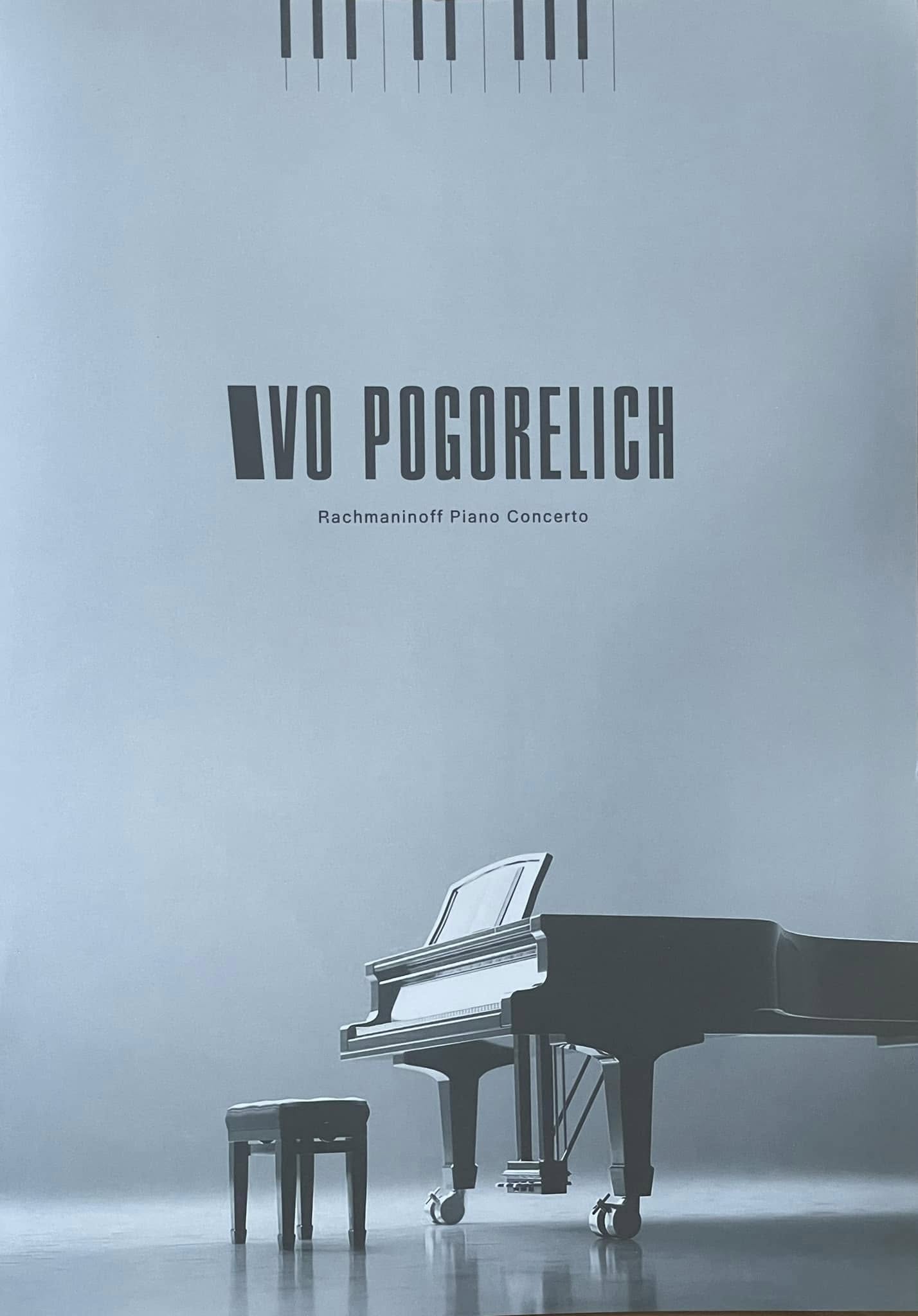
拉赫曼尼諾夫:《C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(作品 18)
在十九世紀前半,葛令卡(M. Glinka)奠定了俄國音樂創作的基礎。葛令卡辭世的1857年之後,俄國音樂開始蓬勃發展。首先,玻羅定、穆索斯基等五位作曲家組成的「俄國五人組」,就在1857年開始活動。再過幾年,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兩座音樂學院相繼被創立(1862年與1866年)。
「俄國五人組」的成員,幾乎都是自學的業餘作曲家,他們推倡富於民族風格、自由創新的曲風;兩座音樂院的教學,比較是著重於西方、尤其是日爾曼音樂的發揚。柴科夫斯基(1840-1893)是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第一批學生之一,畢業後成為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師,也是俄國音樂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第一位重量級的作曲家。
出身於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拉赫曼尼諾夫(S. Rachmaninov, 1873-1943),就像其他一些顯著的「莫斯科樂派」的音樂家一般,經常同時精通鋼琴演奏與作曲。深受柴科夫斯基的影響,拉赫曼尼諾夫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,延續著西方浪漫音樂的傳統的同時,他的樂曲中經常自然而然的流露著深沈、感傷的斯拉夫精神。
在二十世紀初,大膽、創新的種種「現代音樂」傾向的名家輩出之際,拉赫曼尼諾夫堅持著他的音樂中固有的旋律性與抒情效果,看起來好像不合時宜,卻跳脫了現代音樂的艱深難懂,而能夠雅俗共賞的廣受喜愛。
受到柴科夫斯基的鼓勵,原本想在鋼琴演奏上尋求發展的拉赫曼尼諾夫,在莫斯科音樂院學習期間,就積極的嘗試創作;《升F小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》(作品 1)就是學習時期的作品。畢業之後,1897年《第一號交響曲》(作品 13)演出的失敗,卻使得心緒敏感、求好心切的拉赫曼尼諾夫,蒙受了心靈上的創傷,而暫時不再作曲。
幸好在心理醫師達爾(N. Dahl)的悉心照料之下,後來終能重新提筆,在1900年與1901年之間創作了《C小調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。此曲演出的成功,使他掃盡陰霾,重拾信心,此後的1901年至1917年之間,成為他一生中,成果最豐碩的創作時期。
具有相當傳統三個樂章的這首第二號協奏曲,作者宣稱是受到蕭邦、李斯特、柴科夫斯基同類作品的啓發。不論是那個樂章,到處都流淌著美好而充份抒情的旋律。「所有大師們的音樂,都致力於旋律本身的經營,旋律成了音樂的首要。對我自己而言,旋律是我音樂創作的根源,先有了旋律,再衍生出和聲來….」,拉赫曼尼諾夫如是說。
拉氏寬厚的旋律,被配上充分共鳴的厚重和聲,旋律與和聲交融無間;再加上傳承自李斯特的鋼琴高度的炫技,受到管弦樂的推波助瀾;所有這些浮誇的效果,共同渲染著俄式的、斯拉夫民族的濃重抒情與感傷。這種「無可救藥的浪漫」,有誰能夠不望風披靡、望洋興嘆?
第一樂章:中板(Moderato)
從小聲開始,逐漸增強,鋼琴奏出有如大鐘搖擺、充分共鳴的音響。這八小節導奏帶出了由弦樂主奏、鋼琴伴奏,深沈、恢宏的第一主題。此主要主題分成幾個階段被加以延伸、變化,形成第一主題區之後,轉換到對比性的第二主題區:鋼琴獨奏呈現出的沈靜、抒情的第二主題,逐漸上揚,然後又緩和下來。發展部中,鋼琴與管弦樂自由互動之際,充分的發揮種種炫技效果。第一主題的重現,做出有如進行曲般的誇大效果;第二主題則是在弦樂微弱震音的伴奏下,由法國號獨奏引出。到了尾聲,總奏才熱烈的揚起,壯濶的結束。
第二樂章:綿延的慢板(Adagio sostenuto)
充分抒情、歌唱的 A B A 三段體形式。弦樂與木管交融的細膩、感傷導奏,預現出A段悲歌的性質。悲歌的主題先被長笛唱出,單簧管加以複述,最後才由鋼琴主奏充分發揮。由低音管與鋼琴叠在一起,帶出的B段主題,顯得徬徨、無所適從。B段結束於鋼琴獨自發揮的「華彩段」(cadenza),最後再回到A段自由的重現時,A段的悲歌特質已經感染了B段的徬徨,而顯得更加飄盪、憂鬱。
第三樂章:詼諧的快板(Allegro scherzando)
奏鳴曲式,強勁節奏、小調的第一主題,有如俄國民間舞蹈的音樂;它一再的生動變化,形成「第一主題區」。由雙簧管獨奏唱出的柔和主題,逐漸延伸、擴大成充分抒情的整個「第二主題區」。兩個主題分別在發展部被處理的更加自由、開濶,提供給鋼琴盡情炫技的可能。回到再現部後,原本抒情、歌唱,略帶感傷的第二主題,被轉換成贊歌般,莊嚴、厚重的大調音樂,一直通抵燦爛的尾聲,而揮別了先前的感傷、陰影。
德弗札克:《E小調第九號交響曲「新世界」》(作品 95)
音樂風氣興盛的東歐波西米亞(現今捷克的大部分),素有「歐洲的音樂學院」的美稱,因為,從十八世紀以後,當地培養出來的許多優秀音樂家經常「輸出」國外,成為西歐各地許多宮廷爭相羅致的對象。到了十九世紀後半,波西米亞音樂的普及,甚至連出身於鄉下一個經營小客棧、兼營肉舖家庭的德弗札克(A. Dvořák, 1841-1904),自小就有機會接受音樂教育,稍後能繼斯梅塔納(B. Smetana, 1824-1884),成為發揚波西米亞民族風格的作曲家。
然而無論是斯梅塔納或德弗札克的民族作風,都是建立在穩固的日爾曼音樂基礎之上 – 波西米亞長久受到奧國的統治,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,才逐漸興起「民族主義」的風潮,強調本土政治、文化的重要。同是十九世紀後半波西米亞民族主義或「國民樂派」的主要作曲家,聯篇交響詩《我的祖國》的作者斯梅塔納,比較受到李斯特自由、浪漫曲風的影響;至於寫作了九首交響曲及許多其他各類器樂曲、聲樂曲的德弗札克,雖然也不無受到李斯特的啓發,他的作風卻比較傾向於布拉姆斯式的穩健、紮實;也就是說,充分受到古典精神節制的浪漫。布拉姆斯是德弗札克的偶像與好友。
如同貝多芬、舒伯特、布魯克納、馬勒一般,德弗札克總共創作了九首交響曲,但他自認為前四首尚屬習作的水平,而未出版;後五首生前已出版的,即第五號到第九號,全部完成於1875年認識布拉姆斯之後 – 它們顯然是受到後者啓發,開了眼界之後譜成的,較大格局、較深刻的作品。
1892年,德弗札克受「紐約國立音樂學院」的邀請,擔任院長,而在美國居留三年。該音樂院顯然想藉助於德弗札克的經驗,推展美國方面結合本土與西方技法的音樂創作。德弗札克於1893年前半,譜寫了《E小調第九號交響曲》,同年年底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首演。此曲由於體現出壯濶美國的山川文物、風土民情,後來被冠上了「新世界」的標題。
然而「新世界交響曲」旨不在直接的復現美國本土固有的民間音樂,而是相當抽象的,同時體現出美洲與波西米亞的一些「民族音樂」的特徵,諸如調式旋律、五聲音階,富於活力的附點音符,不規則的節奏、持續長音(drone)等。專家學者們 的研究發現,此曲有些旋律或節奏,有些是受到美國「黑人靈歌」(negro spiritual)或印弟安人音樂的啓發,有些則源自歐洲民間音樂。
第一樂章:具有導奏的奏鳴曲式
沈靜、隱約的弦樂帶出小調的慢板導奏,彷彿對未知「新世界」的疑問與好奇;音樂突然變得強烈,好像從好奇到驚訝;平緩下來之後,一個未成型的主題從低音域逐漸浮現,終於成為快速段落(奏鳴曲式的主段)明確、輕快的第一主題。由法國號獨奏引出的第一主題,逐漸延展開來,好像引領人們放眼大地的欣欣向榮一般。第二主題群的前、後兩個主題,前主題具有歐洲波爾卡舞曲般的韻律,渲染著鳥語花香的鄉間風情;後主題則是先前第一主題的變形,它將音樂帶回「大全景」。以上三個主題,在發展部與再現部中,一再的重現、變化,推出更寬濶的視野。
第二樂章
此樂章著名的主旋律,後來被填上「念故鄉」的歌詞而傳播廣遠,然而作曲者原來想傳達的意念,與思鄉情懷可能存在著相當的差距。德弗札克在美國閱讀作家朗費羅(H. W. Longfellow, 1807-1882)的史詩《希亞瓦塔之歌》(The Song of Hiawatha, 1855年),獲得靈感而創作這個樂章。
這部長詩敘述北美印弟安人的傳說,原詩中的一個森林中葬禮的情景,就是此樂章靈感的源頭。銅管樂器莊嚴而深沈的合奏,帶出了寬濶而徐緩(Largo)的A段;音色有些灰暗、深沈的英國管,吟唱出高貴而略帶感傷的降D大調主旋律;此飄逸悠遠的旋律,據說是受到美國愛爾蘭裔住民歌謠的啓發而譜成的。旋律幾經延伸、起伏,轉換成整個樂章的中段。中段的前半,由長笛與雙簧管引出一段「稍微變快」、比先前陰鬱、抒情的旋律;中段的後半,由雙簧管帶出有些斷音、節奏比較明顯的「田園風」音樂,悲情彷彿融入大自然中,被稀釋了。突然間,銅管合奏出A段旋律開頭的片段;A段英國管的旋律重現之後,逐漸變得輕靈、飄忽,最後在銅管小聲的「合唱」中消失了。
第三樂章:活躍的詼諧曲
此樂章也是與朗費羅的史詩有關,活潑生動的音樂體現出原著中,印地安人「森林中的節慶」。整個樂章可約略的細分成A B A C A B A六個段落。A B A是詼諧曲的主段,後面的 A B A是前面主段的復現;正中間的C段是「中段」。A段跳躍般的律動,偶爾被不規則則的節奏加強了生動的感覺,令人聯想到貝多芬《第九號交響曲》詼諧曲樂章的效果。速度放慢些,變得比較緩和、細緻的B段與C段,應該是源自波西米亞民間的舞蹈音樂。
第四樂章:熱烈的快板,奏鳴曲式
深沈、威猛的弦樂奏出漸強的簡短導奏,帶出了銅管合奏的壯濶第一主題,徬徨宣示著勇猛精進的大無畏精神。第一主題經過延伸、擴充之後,單簧管獨奏出沈思的第二主題,好像引領人們去見識新世界美好的底蘊。在發展部中,不只此樂章已被呈現的主題,連前三個樂章的一些主要主題,全都被當做充分發揮的材料。第二樂章英國管的主題尤其被強調,去除了原本的感傷,而變得明朗、開放。進入再現部後,音樂變弱,好像做著深遠的回顧;到了尾聲,音樂再度揚起,奏出強勁的總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