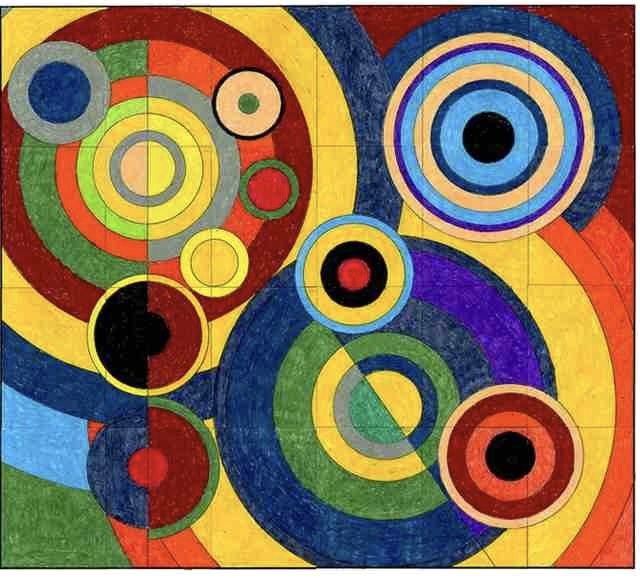蕭邦的音樂-鋼琴的靈魂
波哥雷里奇的兩場獨奏會已結束,不知曾經去聽的人有沒有什麼感覺?
現在把我寫的樂曲解說全部貼出來,讓沒去聽的人也可以參考一下。
人們經常稱蕭邦為「鋼琴詩人」,然而在十九世紀,鋼琴音樂大行之道的時代,鋼琴詩人可能就不只有一位 – 從貝多芬、舒伯特開始,經孟德爾頌、舒曼、蕭邦、李斯特,到佛瑞、德布西、史克里亞賓等,那一位不曾藉著鋼琴,表達著不具詞語的無言詩意,抒發著各異其趣的浪漫情懷?在這一群鋼琴詩人中,蕭邦的顯得獨特,主要在於,他能窮盡短暫一生,聚焦在鋼琴音樂上,藉著鋼琴,渲染出純粹、微妙的內心世界,使得天才的靈魂與鋼琴的靈魂形成共鳴,融合無間。
與他的摯友李斯特背道而馳,內向的蕭邦不喜歡大庭廣眾的公開音樂會,而偏好私密場合的沙龍聚會,在精英份子之前,藉著鋼琴傳達他的藝術。以下是德國作曲家希勒(Ferdinand von Hiller),旅居巴黎時的見證:「蕭邦平時甚少盡情表露,但一坐到鋼琴前,就是全然的沈緬,沒有任何俗事能夠干擾他;這點,沒有其他音樂家能夠與之比擬。」
除了少數幾首管弦樂、室內樂、歌曲,蕭邦的創作幾乎全是鋼琴獨奏曲;而那些少數例外的樂曲,也都有鋼琴的介入。「標題音樂」大行其道,藝術家們熱衷於將音樂與文學、戲劇、美術等融混在一起,尋求豐富、多變化的效果之際,蕭邦却專注於抽象的、細緻的純粹音樂裡。許多作曲家紛紛在鋼琴中尋求管弦樂團般「交響化」效果的同時,蕭邦則是探尋鋼琴靈魂的深處,藉著鋼琴,進行著自然、飄逸的器樂歌唱,窮究著鋼琴音響、色調的漸層變化,開發著鋼琴的種種潛能 – 在他辭世之後的十九世紀後半,有那位鋼琴作曲家,能夠不受到蕭邦的啓發?
1831年,二十歲的蕭邦,在出國旅行演奏的途中,驚聞「華沙起義」以失敗告終。蕭邦從此旅居巴黎,不再返回祖國波蘭,不時藉著他的馬厝卡舞曲、波蘭舞曲,抒發著熱烈的愛國情操與思鄉的感傷。這些都是事實;然而人們在強調歐洲北方人的蕭邦是「波蘭的靈魂」與他的「斯拉夫精神」之際,卻經常忽略了他其實也流著法國的血液,經常嚮往著歐洲南方的「拉丁精神」。
蕭邦(1810-1849)出生、成長於華沙,他的母親是波蘭人,父親則是從法國洛林地區來到華沙,專門教授法文的移民。蕭邦後來旅居巴黎,終生不再返回波蘭,更在這個人文薈萃的首都,充份的融入相當多樣性的文化、藝術氛圍中。如此的身世與經歷,使得蕭邦成為北方與南方藝術的見証者與融合者,令人驚嘆的是,蕭邦式的融匯貫通,是那麼的均衡,那麼的完美!
例如,蕭邦獨樹一幟的「鋼琴歌唱」,經常被俗稱為「如歌的」(cantabile ),主要是源自當時大行其道的義大利歌劇 – 羅西尼、貝里尼風靡各地的「美聲風格」,使得自小喜歡歌劇的蕭邦沈迷其中。蕭邦尤其受到貝里尼相當優美、飄逸的,所謂「平順唱腔」(spianato)的啓發,將聲樂的旋律,轉化成器樂的旋律,使得鋼琴不具歌詞的歌唱,嚮往著「一切盡在不言中」悠遠、崇高的詩意。南方相當官能性義大利歌劇「美聲」的享樂主義,就這樣被蕭邦昇華成非常心靈的、精神性的境界;這種心性的、抽象的「絕對美感」(absolute)的憧憬,無疑是比較傾向於「北方浪漫」的精神。如歌的鋼琴歌唱,經常在精緻、剔透的和聲,𩆜巧、生動的節奏,相輔相成之下,被蕭邦經營成「心醉神迷」(ecstasy)般的高潮;這種迷醉之美,使得北方激情、暗鬱、放縱的悲愴,被南方精神稀釋的相當澄澈、優美、節制,而符合了法國藝術傳統中經常標榜的「美好的品味」(bon goût)。
成長於演奏名家輩出,炫技蔚成風氣的十九世紀前半,從小已是鋼琴神童,兼擅即興演奏與作曲的蕭邦,自然而然的就成了「炫技名家」(virtuoso)。在華沙與巴黎相繼聽到義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非凡的演奏,「超絕技巧」(virtuosité transcendante)的理念,更深植蕭邦心中 – 炫技不只是為了譁眾取寵的目的,而是用來表達敏鋭性與情感變化的手段;技巧必須超脫炫技之上,用來成就藝術。蕭邦經常在沙龍音樂會上即興彈奏,展現非凡的技巧;但是即興演奏之後,經過深思熟慮的整理,使得直覺、感性的樂思,經歷理性的焠鍊,才是完善的創作,就像把野馬加以馴服,把粗糙的石塊打磨出細緻、平滑的紋路一般。
聽聽蕭邦所有作品中,許多快速音群,連續八度、三度、六度的段落,所做出的很含蓄的炫技;恰到好處,用來增益旋律表現力的簡潔裝飾音;自然、流暢的指法安排;精巧設計,卻不浮濫的踏瓣效果;以及那著名的「彈性速度」(tempo rubato)的運用。所有這些效果,共同成就了兼具放縱與節制、野性與優美、感性與理性的,北方與南方的,無與倫比、近乎完美的「蕭邦風格」。
關於著名的「彈性速度」,經常遭到誤解,例如蕭邦的好友白遼士形容它是「放任的太多,流失了節拍的韻律感」。或許白遼士不是鋼琴家,才產生如此的誤會;蕭邦的另一好友李斯特,是最好的鋼琴家,才能道出彈性速度的獨特:「注意觀看那些大樹,微風輕拂樹葉時,形成了葉浪的波動起伏,但樹幹是不動的,這就是蕭邦式的彈性速度。」 也就是說,蕭邦在做彈性速度時,旋律形成了短暫的快慢、自由的變化之際,墊底的節拍、韻律卻必須穩住節奏感;將放縱與嚴謹綁在一起彈奏,這就考驗日後許多詮釋者的音樂性了。
知名鋼琴家波哥雷里奇,新近推出的一張蕭邦音樂全集的錄音(SONY 194399120521),據說「是他二十年來再度發行整張蕭邦作品的專輯」,而受到相當的矚目。順著推片的氣勢,波哥雷里奇展開了包括台北、高雄兩站的世界巡演。無論是錄音或巡演的曲目,波氏聚焦在蕭邦最後數年中,一些格局比較大、起伏比較充分的作品,或許是順水推舟的,用來發揮他的獨特演奏風格。

有著「壞孩子」(enfant terrible)之稱的波哥雷里奇,總是以驚世駭俗的放縱詮釋激起議論。這次他一樣走極端,嘗試以蕭邦個性比較鮮明的一些樂曲,「藉極度的晦暗,反襯出高遠的光芒」,並且甩開其他一些鋼琴家們過度甜美討好的平凡演奏。波哥雷里奇突顯自由放任極端的同時,是否能兼顧蕭邦音樂固有的優雅、細緻與澄澈,而形塑出壯濶的完美?我們且等著聽吧!
《降A大調波蘭舞曲-幻想曲》(作品 61)
蕭邦宛如流星般短暫、絢爛一生的音樂創作,始自七歲的一首波蘭舞曲,終於三十八歲的最後一首馬厝卡舞曲;質量俱豐的這兩類舞曲的創作,可見他對波蘭淵源的珍視。就數量而言,蕭邦的十六首波蘭舞曲,不像五十七首馬厝卡舞曲那麼多,波蘭舞曲卻相當平均的被創作於從童年到過世前的各個時期。
波蘭舞曲(polonaise)與馬厝卡舞曲(mazurka)不同之處在於,「波蘭舞」是盛行於古時上流社會,穩重莊嚴的宮廷舞蹈,「馬厝卡舞」則是通俗活潑的民間舞蹈。蕭邦根據這兩類傳統舞蹈創作音樂,發揮各自的特徵之際,卻將它們充分的「藝術化」了 – 將音樂創作的相當自由、抽象,富於變化,而超脫了原本伴奏舞蹈的功能。
在古代波蘭貴族的舞會中,波蘭舞是用來當做開場的團體舞,盛裝的舞者們,列隊緩緩前行,舞姿優雅莊嚴,炫示排場的效果十足;3/4拍子、不疾不徐速度的音樂,短音符與附點音符推動著的韻律,加強了雄赳赳、氣昂昂的效果。蕭邦將這些特質,相當自由的加以渲染,經營出交錯著激越、陰沈、明亮、感傷、憧憬的種種情緒變化,用來表達波蘭人民受到侵侮的共同心聲,以及他對遙遠袓國的懷念。
創作於1846年的《降A大調波蘭舞曲-幻想曲》(作品 61),是蕭邦十六首波蘭舞曲的最後一首。「波蘭舞曲-幻想曲」(Polonaise-Fantaisie)的法文標題,在國內一直被譯為「幻想波蘭舞曲」,有違原義,所以將它調正過來。此曲之所以如此稱呼,因為它即是波蘭舞曲,同時也是幻想曲 – 具有波蘭舞曲的韻律特徵,以及幻想曲相當天馬行空的自由形式。
比起其他的波蘭舞曲,此曲具有較大的規模;音樂游移在大格局中,曲風相當放任、不可捉摸;節奏明確的段落與不明確的段落交錯出現,明確之處經常只是短暫的靈光乍現。全曲有如行雲流水般的體現出晚年蕭邦孤寂落寞的心境變化;它的狂想式的特質,令人聯想到李斯特的一些「匈牙利狂想曲」。然而,李斯特的狂想曲,炫技做的比較明顯,戲劇起伏做的比較大起大落;蕭邦的幻想曲顯得比較深沈、內斂。
《B小調第三號鋼琴奏鳴曲》(作品58)
蕭邦兩百多首鋼琴曲中,大部分是規模較小、內容精緻的短曲,大格局的樂曲,諸如敘事曲、詼諧曲、幻想曲,尤其是奏鳴曲,只是少數。在蕭邦所處的浪漫盛期,一般作曲家們都不太想碰觸大型樂曲,只因為不久之前,貝多芬已將大型樂曲的創作,推到難以踰越的高度;在貝多芬巨大的「陰影」籠罩之下,浪漫作曲家們紛紛另闢蹊徑,「小品」的創作反而成了顯學 – 那是在貝多芬之前,尚未被充分開發的一個領域。比起他的同僚們,蕭邦似乎沒有那麼在乎「貝多芬的陰影」,總共譜寫了三首各具四個樂章的鋼琴奏鳴曲。鋼琴家、音樂學家羅森(Charles Rosen)認為:蕭邦成長於音樂主流邊緣的地方(指波蘭),所以較未注意到貝多芬式的「威脅」。
蕭邦的三首鋼琴奏鳴曲雖建構在古典的框架上,卻經常突破古典的藩籬,不時洋溢著自由的詩意、敏鋭的感興。如果《C小調第一號奏鳴曲》(作品 4;1828年),還是年輕時的習作;十一年後的《降B小調奏鳴曲》(作品 35;1839年),也就是具有〈葬禮進行曲〉樂章的那首,已是個性鮮明,悲愴效果十足的名曲。再五年後的《B小調第三號奏鳴曲》(作品 58;1844年),好像刻意擺脫第二號的悲劇性,嚮往著超脫現實的絕美境界。
《第三號奏鳴曲》創作、完成於1844年之際,蕭邦剛與他的情人喬治·桑分離,晚年病痛的威脅也逐漸加深;然而它卻有別於第二號的陰鬱與激情,而是以超脱的心態,表達出相較之下顯得客觀、清醒的境界;這個境界有如一個想像中的美好風景般的遙不可及;在這此境界中,蕭邦的「南方」屬性無疑佔了上風,將他的「北方」特質適度的抑制著。此曲雖然以B小調為主調,但是小調的呈現,經常是短暫的,它的陰影,經常被大調的微光驅散;小調與大調的游移、不明確,為此曲增添了曖昧、幽遠的詩意。
第一樂章,「莊嚴的快板」,奏鳴曲式。
強勁、感傷的第一主題,很快就消沈下去,取而代之的第二主題,具有典型蕭邦鋼琴歌唱的種種特徵:貝里尼歌劇旋律般的蜿蜒、縹渺,適度的裝飾音與彈性速度。此後,第二主題將主導整個樂章,第一主題甚至在再現部中不再重現。
第二樂章,詼諧曲。
主段與中段都是大調的(降E大調與降B大調);主段的輕靈活躍、滔滔不絕,與中段徐緩、微妙和弦銜接的沈思效果,形成對比。
第三樂章,寬廣的(Largo)。
以B大調為主調的、徐緩的器樂歌唱;寬濶、飄逸的段落,與抒情、夢幻的美聲歌唱段落交替出現;三連音伴奏下的夢幻樂段,有如浮動著波光的威尼斯船歌般。第四樂章,「不過分的急板」(Presto non tanto)。具有簡短而強勁導奏的迴旋曲。有如奔馬疾馳的重現段(A段),每次再現時,都顯得更迅速,介於重現段之間的變化段(B段、C段 …),每段顯現時,一再呈現出新穎的效果。全曲結束於充分炫技的尾聲。
《F小調幻想曲》(作品 49)
從1841年初開始構思,完成於同一年十月的這首幻想曲,顯然是是部相當自由放縱,悲愴焦慮的創作;樂曲順著幻想曲式的本質,洋溢著即興揮灑的狂烈本性,經過蕭邦深思熟慮的整理之後,音樂中蘊藏著細密樂思的擴充、發揮,巧妙、大膽的和聲與轉調;對比性的樂段無拘束的交錯出現,渲染著情感大起大落的變化。
此曲剛完成之時,蕭邦在寫給他的好友封塔納(Julian Fontana)的信中提到:「今天我剛完成了一部幻想曲,天空依舊湛藍,我內心卻充滿憂戚。這或許沒什麼關係,假若不如此的話,我的存在對人們可能就沒什麼意義吧!」
全曲由一段「進行曲風格」的導奏展開,徐緩的步伐,小調的感傷,附點音符的韻律,顯然是段葬禮進行曲。接著的主要段落,在疾速三連音的推動下,逐漸激起了內心的風暴。風暴逐漸平緩下來後,音樂由原先的4/4拍子,轉換成3/4拍子,「綿延的緩板」(Lento sostenuto ),那是宛如聖詠(choral)般的沈思默想。到了全曲尾段,快速的激烈音樂又起,幾經浮沈,最後終止於感傷的尾韻中。
《降D大調搖籃曲》(作品 57)
此曲大約創作於1843年,出版於1845年。蕭邦自己稱之為「變奏曲」(Variantes) – 簡短四小節的徐緩主題,經過十四次變奏後,結束於尾聲。在低沈、神秘和聲的伴奏下,6/8拍子韻律的輕搖下,右手做出種種裝飾音、音階、琶音、三連音、六連音、顫音、倚音的細微變化;全曲的飄忽、神秘、超脫,彷彿把睡眠昇華到至高的靈性境界。
左手奏出的和弦伴奏,在主、屬和弦之間搖擺著,透過輕柔的彈奏,以及踏瓣的巧妙應用,成了失重狀態。連串平行三度音的半音級進,帶出了縹緲、夢幻的效果。第三、四、五指的交叉彈奏,更把細膩的音響,撫摸的如夢似幻 – 如此的指法應用,在當時是新穎、前瞻性的。
《升F大調船歌》(作品 60)
威尼斯船夫在夜光下擺渡歌唱的情景,是浪漫時期藝術家們深深著迷的意象,作曲家們一再以「船歌」(Barcarolle)渲染出波光蕩漾,輕柔歌聲飄揚的詩意。蕭邦在1845-1846年之間完成的唯一船歌,稱得上較具前瞻性與「現代感」的作品之一,以下是拉威爾的關於此曲的描述:「三度平行的柔和旋律,被配上多彩的、一再翻新的和聲(主段)…..。旋律卻逐漸飄逝了,連串令人驚異的和弦,激起了張力(中段)……。平緩下來之後(主段具有相當變化的重現),從低音區昇起一悸動著的快速音群,翱翔在更加細緻的和聲上,宛如進入神秘的夢境般。」
這首夢幻般的船歌,其實是以「夜曲」(nocturne)的三段體形式,以及它的夜間美好意境當做基礎,再輔以船歌的輕柔搖擺的韻律(12/8拍)。兩者相輔相成,共同渲染出心醉神迷般的詩興蕩漾。三段體的中段,將迷醉推向極致,平緩下來後,好像經歷了一場美夢般,夢醒之後感到有些悵然。